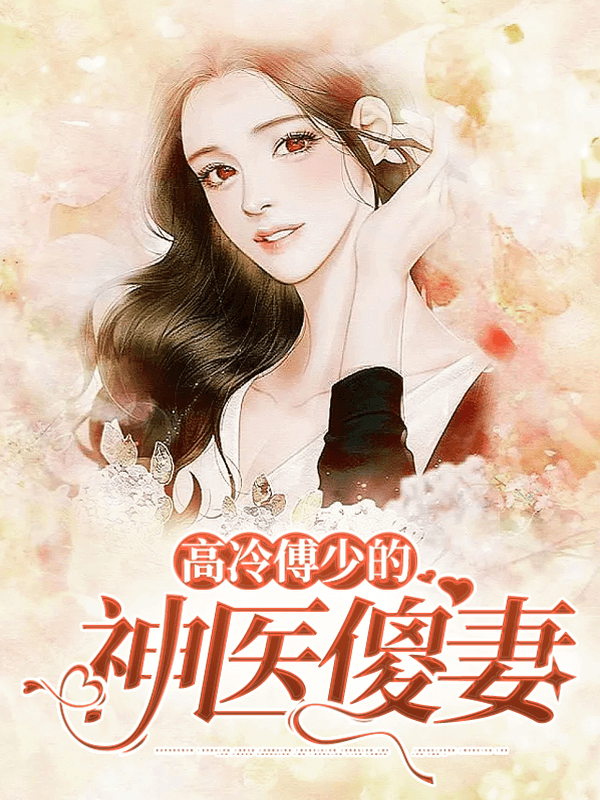單單昨晚上官蘊昨晚的熱情,景純就敢篤定他不像外界傳聞的那般是個病秧子,既然這樣的話,那就很有意思了。
「你如果亂說話,整個景家都會因為你陪葬。」
清淡恬闊的語氣,景純卻不自覺的顫了顫,雖然她對景父和那個名義上的姐姐沒有任何溫情,但景家還有她的軟肋在。
上官蘊的目光瞬間落到景純臉上,寒冷而帶着壓迫性:「把床上的落紅處理掉。」
景純打了一個寒顫,心裡愕然一涼。腿間傳來的疼痛時刻提醒着昨晚戰況有多刺激。
"怎麼,你還要毀滅證據?"景純目光杳然掃過床上的落紅,心裡一陣刺痛。
女孩子最珍貴的初次,就這樣莫名其妙的給了一個陌生人。
上官蘊低垂眼瞼,渾身都散發着低氣壓:"難道你想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昨晚被我上了?"
景純一臉窘態,又羞又怒地咬唇道:「你這樣未免太過分!」
「過分?」上官蘊唇畔嚼着一抹冷冷的笑意,語氣森寒,「我還有更過分的!」
上官蘊臉部的線條略顯冷硬,不緊不慢地邁着步子向景純逼近。
景純感到撲面而來的壓力,全身僵硬,聲音顫抖着道:「別過來!」。
她剛想退後,門外便傳來聲音:「大少爺,老夫人請您和太太下去參加家宴。」
景純瞬間瞪大眼睛,緊咬下唇看着那床上的落紅,心虛地呆在原地。
催促聲還在繼續,上官蘊冷冷瞥了景純一眼,而後當機立斷地從柜子里翻出剪刀,抬手奪過床單,將落紅利落剪掉。
在景純還未反應過來時,耳畔就傳來男人虛弱的聲音:「好,咳咳,我知道了。」
上官蘊聲音虛弱而低沉,把久病之人的聲音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應付完傭人,上官蘊朝着景純勾了勾食指,示意她靠近。
景純疑惑的走近,而後上官蘊驚心動魄的咳了起來,臉色蒼白如紙,十分駭人!
「上官蘊,你沒事吧?」景純明顯受到了驚嚇,如果她嫁過來第一天上官蘊就死了,那她肯定也沒有好果子吃。
"藥在第二個抽屜。"上官蘊臉色雖差,卻眼神清明,冷厲的氣勢壓迫着周遭的一切,包括景純。
景純手忙腳亂去拿藥幫她服下,而後看着男人臉色恢復了幾分血色後平緩了一下心情:「上官蘊,你不去演戲真是可惜。」
上官蘊不咸不淡地瞥了她一眼:"是不是昨晚沒餵飽你,讓你現在還有力氣在這裡和我鬥嘴?」
景純立刻識趣的閉嘴,那種痛,她不想再品嘗第二次!
收拾妥當後,景純和上官蘊一起出現在大廳。
景純扶着上官蘊下樓時,便接收到太多異樣的目光,所以她每一步都走的極其細緻,指尖忍不住發抖卻出賣了她的真實內心。
抬眼看着窘迫的女人,上官蘊心裡忍不住軟了軟。
一陣冰涼的觸覺從掌心傳來,又涼又癢。
景純抬頭仰視,卻見上官蘊清俊的臉上表情淡然。
白欣坐在主位,手裡接過景純的奉茶卻直接扔在了她臉上:「掃把星,你是用了什麼狐媚手段勾搭我兒子,害他新婚第一天就發病?」
滾燙的茶水立刻將景純白皙的皮膚燙出一片潮紅,景純無力反駁,手臂上灼燙感異常,她卻緊咬着下唇沒有發出半點聲音。
抬眸不經意的打量着盛氣凌人的婆婆,分明上官蘊在房間裡和她做的一場戲,怎麼會這麼快就傳到白欣耳朵里?
細思極恐,這個上官蘊是刻意讓她難堪。
而白欣這個做母親的,深知自己兒子早上不舒適卻立刻讓他來參加家宴?
沒等她想好措辭應對,耳畔立刻又傳來白欣尖酸刻薄的質問:"景思,你不是向來體弱嗎,這會兒我怎麼看的都不像病弱的樣子?"
聞言,景純的臉色變得難堪不少,心裡咯噔一下。白欣已經開始懷疑她的身份了,而那恰恰是她的死穴。
須臾,她撣開手臂上的茶葉,不卑不亢的迎上白欣的視線:"這麼說,婆婆既然知道我體弱多病還要我去照顧上官蘊,這不是故意害他嗎?"
話落,在場之人無不面面相覷。
白欣被景純的話堵到,她沒想到這個景思居然如此乖張,"景思,你爸把你嫁過來是為了照顧好我兒子的,不是讓你來這裡養尊處優的!"
景純用餘光瞟上官蘊,卻瞥見他淡定地喝着茶,察覺到他的視線也不為所動。
她把視線投向全場,心一點一點地沉了下去。
參加這場家宴的都是上官家的人,她一個外來女人,沒有人會幫她。
白欣觀察到景純孤立無援,臉上露出一抹嘲諷。
隨後神色一厲,白欣提高聲量發出最後通牒道:「啞巴了?要是說不出原因,你就滾回景家去!上官家不需要掃把星!」
「母親先不要着急下定論。」
清冽卻病弱的嗓音傳來,景純抬頭凝視上官蘊,想看看這個怪異的新婚老公會如何應對。
白欣的目光落到上官蘊的臉上,冷酷中帶着審視,又很快轉化為慈愛,眼中含笑用柔和的語調問道:「蘊兒有什麼話說嗎?」
「嗯。」
上官蘊微微點頭,揚起一雙清冷黑眸,沉聲道:「今天是我自己的身體原因,不怪思思,還請母親不要怪罪她。」
白欣只好悻悻地瞥了景純一眼,眼神飽含警示。
景純主動移開目光,長長的睫毛掩蓋住了她眼底的隱忍,不與白欣對視。
白欣的目光極具穿透力,凌厲地瞪向景純,道:「景思,如果做不好上官家的兒媳婦,那就趁早滾出去!」
語落,白欣高昂着頭離去離去,這場家宴最終不歡而散。景純對上官家的事情算是越來越迷糊了,有一團迷霧始終擋在她面前。
她只能確定一件事情——這裡很危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