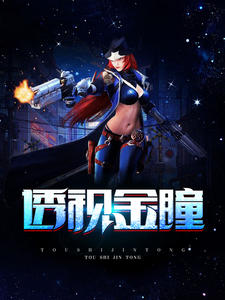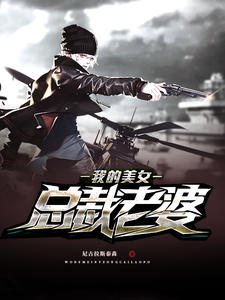正是晌午時分,酷熱的日頭掛在當空,蟬鳴聲兒在樹林間此起彼伏。這一會兒,莊稼漢們全都吃飽喝足,躺在自家涼蓆上,打着蒲扇闔眼午歇。
程氏躺在涼蓆上,面向牆壁,背對着男人宋長生,悄悄摸着懷裡那大塊的銀錠。程氏這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麼大塊的銀子,又白又亮,冰冰涼涼,好不惹人喜歡。
「嗬啊!」宋長生打了個鼾聲,翻了個身子,仰面躺在床上。一條死沉的大腿搭在程氏腰上,壓得程氏悶哼一聲,扒着他的大腿費勁地抬開。誰知宋長生竟又翻了個身,手腳並用把她摟在懷裡。程氏氣壞了,使勁捶宋長生:「死人,起開,你想熱死我呀?」
宋長生被捶醒了,半睜開眼,粗憨的聲音道:「你這婆娘,捶我做啥?想死啊?」
「你才想死哩!鬆開我!」程氏使勁掙扎。
宋長生有些醒了,嘿笑一聲,不僅沒有鬆開程氏,反而翻身把她壓在身下:「你那個走了吧?咱們可是有些日子沒有……」
「咋胡來呢?大白天的你想做啥?」程氏慌了,卻不是當真怕這檔子事,而是怕宋長生髮現她懷裡藏着的銀子。
從鳳氏院子裡搶了銀子這事兒,程氏誰也沒有告訴。宋長生是個賭鬼,若知道這筆銀子,定然摸去耍賭。而婆婆朱氏刻薄精明,給她知道這筆銀子的存在,定然收上去一文錢也不留。
上午的時候,程氏躲在樹後瞧得清楚,鳳氏被那男人一腳踹飛,連牆壁都撞塌了,不死也去半條命,定然沒有精力來鬧。這十兩銀子,便是她一個人的了。
程氏打得好算盤,本來萬無一失。誰知宋長生正值年輕力壯,只見身下程氏扭動得有趣兒,愈發嘿嘿笑起來。這一番你掙我按,程氏亂了髮髻,鬆了衣裳。藏在懷裡的十兩銀子,也骨碌碌地滾了出來,掉落在涼蓆上。
「這是啥?哪來的?」宋長生眼疾手快,一把抓到手裡。
程氏頓時急了,宋長生是個賭鬼,而且是十賭十輸的那種,這十兩銀子落到他手裡,便等於打了水漂!程氏藏着掖着,防的就是他,如何肯依?拼了命地去搶:「這是別人托我保管的,你還給我!」
「誰這樣有錢,托你來保管?」宋長生壓根不信,把銀子往懷裡一揣,從程氏身上翻下來。
程氏從後頭抱住他的腰,死也不讓他走:「這是我娘給我的!你還給我!」
從未乾過農活的程氏該有多大力氣?宋長生抓住她的手,一把甩開,趿上鞋子便朝外跑去。程氏急得連鞋子也顧不得穿,赤着腳便追了出去:「宋長生!你給我站住!」
宋長生哪裡肯聽?此時已經跑到大門口,身子一閃便竄了出去。程氏氣得直跺腳,不禁罵道:「宋長生!你個天殺的!你不得好死!」
「作死的小娼婦,你罵誰呢?我看你才不得好死!」朱氏的聲音從正房裡傳來,「我們長生哪一點對不住你?你卻如此咒罵他?你是不是外頭有了野漢子?我警告你,你生是我宋家的人,死是我宋家的鬼,既然進了我宋家的門,便沒有再踏出去的份兒……」
朱氏是個精明又刻薄的女人,家裡除了宋長生,無人沒有挨過她的打罵。大姑子鳳氏,未出嫁前更是吃罵聲跟家常便飯似的。此時程氏把宋長生摸了十兩銀子去賭的事告訴朱氏,十有八九還有要回來的可能。可是聽了朱氏的咒罵,程氏情願把銀子給宋長生打水漂!心裡罵了聲老虔婆,扭臉進屋摔上門。
坐在床邊,想起自己冒着挨打的危險,辛辛苦苦搶來的十兩銀子就這麼沒了,不禁傷心地流下眼淚。心中暗暗罵道,該死的宋長生,該死的朱氏!
「哇——」這一番動靜,吵醒了炕頭上睡着的小娃兒,張大嘴巴哇哇地哭起來。程氏走過去,照着他的屁股就打:「哭什麼哭?跟你那死鬼爹是一個德行,索債鬼!我欠你們的啊?吃好喝好伺候着,竟然還跟我哭鬧!」
一歲的娃兒懂得什麼?挨了痛揍,更加哭得大聲起來。正房裡的朱氏被吵得睡不着,揮着蒲扇罵罵咧咧地走過來:「你作死啊?朝我孫子出什麼氣?誰又惹着你了?成日好吃懶做不幹活,還有臉打我孫子?」
一陣高過一陣的尖銳的婦人爭執聲,比那後山的蟬鳴聲更叫人心生厭煩。隔壁院子裡,青磚紅瓦蓋起來幾間高大的房屋,宋如山蹲在檐下吧嗒吧嗒抽着煙袋子。偶爾朝隔壁宋如海家的方向瞄上一眼,在田間勞作了大半輩子,被日頭曬得黑紅的臉上透着一股鬱悶。
宋如海是宋如山的親弟弟,他們爹娘死得早,宋如山累死累活給宋如海娶了個嬌婆娘,沒有想到這個弟弟被婆娘吃得死死的,這些年愈發鬧得不快,雖然住在隔壁,卻幾乎沒了往來。
耳邊傳來宋如海的婆娘打罵兒媳的聲音,宋如山的臉色愈發難看起來。那個侄兒媳婦也不是個好玩意,兩個敗家婆娘天天鬧騰,把宋家的臉都丟盡了。
「奇了怪了,鳳妹子怎麼還不過來?」吳氏的聲音在身後響起,「難不成又打退堂鼓了?不能啊,我上午瞧着她的神情,像是不把銀子要過來就不算完的樣子。莫非出什麼事啦?那姓沈的狼崽子又派人來搶孩子啦?」
宋如山低頭抽着煙袋子,農家漢子粗噶的聲音響起來:「你去瞧瞧。」
「好嘞!」吳氏是個急性子,話音剛落,已經風風火火地衝出屋門,往院門口跑去了。
衝出家門的吳氏,一路往村尾鳳瑤住的地方跑去。心中想道,若是鳳妹子再不爭氣,可一定要勸勸她才行。她就是不為了自己,也要為了豆豆,哪有當娘的不顧孩子死活的?
快跑到鳳瑤家門口時,遠遠就看見路上躺着一個人,豆豆蹲在旁邊,哇哇地大哭。